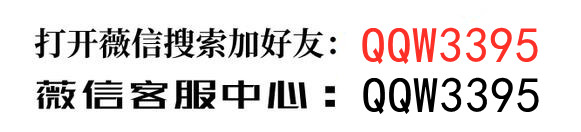在医学院,学生们被教导说:“当你听到马蹄声时,想想马,而不是斑马。”
这是为了提醒医生在诊断患者时首先考虑常见疾病,而不是罕见疾病。因此,今年春天,当我开始感到腹部右上象限疼痛时,我告诉自己要理性。这种感觉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在一次车祸后所感到的疼痛。在谷歌了一番之后,我认为原因很可能是胆结石,没什么可怕的。
我是一名生物学教授,拥有分子、细胞和发育生物学博士学位,在研究生期间研究了肿瘤抑制基因BRCA1(乳腺癌基因1)的调控和促进乳腺癌转移的基因。我在主要是本科院校任教近20年,目前我对学生的研究涉及使用膳食植物化学物质(水果和蔬菜中天然存在的化学物质)作为化疗剂来抑制乳腺癌细胞增殖。
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等几天再打电话预约医生的部分原因——这是学期末,我想把我的最终成绩提交给医生。
但后来我碰巧和一位同事交谈,他碰巧告诉我,一位家庭成员患有癌症,即将结束他们的旅程。我起了鸡皮疙瘩,立刻打电话预约了初级保健医生。
医生最初还怀疑是胆结石。这时,我正经历着剧烈的疼痛。深吸一口气会痛。预约时间是周五,所以胆结石检查要到下周才能进行。我问那天是否可以进行另一种测试。考虑到疼痛的程度,我很担心,我可能要到下周才能回来。
他们告诉我,如果疼痛加重,我应该去急诊室,在那里他们可以立即完成必要的检查。我坚持认为,当天一定要做些什么来评估我的健康状况,而不是求助于价格高昂的急诊科。如果我不为自己辩护,还有谁会呢?
在医生、护士和办公室经理激烈讨论之后,我当天下午做了CT扫描。到了晚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告诉我结果。医生告诉我,扫描显示我肝脏有多处病灶,表明有转移。在我的小肠也有一个可见的肿块。我得了癌症晚期。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诊断。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三个孩子,想到我可能活不到他们高中和大学毕业了。我不能活到退休,也不能和我丈夫一起享受退休时光。我活不到当奶奶的时候。
我重新集中了注意力,问医生下一步该怎么做。我被安排去做肝脏活检,以确定我到底患的是哪种癌症,一旦确定,我就会被转到肿瘤学家那里。
虽然我最初的扫描显示小肠有肿瘤,但恰好有五种类型的癌症发生在小肠中,每种癌症都有不同的生物学特征,在预后、治疗方案和总体生存期方面各不相同。当护士打电话告诉我病理结果时,她结结巴巴地告诉我,我有一个“分化良好的1级神经内分泌肿瘤”。
她漫不经心的语气让我觉得我的测试结果似乎正常。我非常震惊,这就是消息传递给癌症患者的方式,没有任何额外的背景。
幸运的是,如上所述,我碰巧是一名教授癌症生物学和乳腺癌研究的生物学教授。我知道什么是分化良好的1级肿瘤。事实上,在护士打电话的前一天,我已经在网上阅读了病理报告,并开始研究我的诊断,以便我可以做出明智的决定。

神经内分泌肿瘤(NET)是一种罕见的癌症,发生在神经内分泌细胞中,可在全身发现,最常发生在胃肠道、胰腺和肺部。
事实证明,这些蹄声毕竟来自斑马;神经内分泌癌症的癌症意识丝带是黑白斑马条纹。
在与我的肿瘤医生预约之前,我进行了文献搜索,并如饥似渴地阅读。我了解到,尽管我这种类型的肿瘤生长缓慢——鉴于我的阶段——但我的癌症是无法治愈的。我沮丧地了解到,有有限的治疗方案,以帮助延缓进展。我的策略是按照最佳顺序选择治疗方法,尽可能延长我的寿命。
我带着一份问题清单去看肿瘤医生。我渴望了解更多关于我的具体病例和预后的信息,特别是因为我最初的诊断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我非常失望地离开了我的访问,这是轻描淡写的。
当我回想起这次任命时,我越来越生气。虽然他还安排了额外的检查,包括专门的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扫描,可以检测神经内分泌肿瘤,以更准确地评估我的肿瘤负担和预后,但当他讨论治疗方案时,都是泛泛的,不是针对我的病例。
他回避我的问题或给出不明确的回答。我也无法相信,作为一个新诊断的癌症患者,我没有得到任何资源来咨询关于神经内分泌肿瘤的进一步信息。
如果我不是癌症生物学家呢?如果我在任命期间只得到最少的信息,我就会非常无知,对未来的决定也准备不足。
我试着不去生气,相信他是无辜的。当然,一旦他得到PET扫描结果,并与肿瘤委员会的其他医生讨论,一个行动计划就会实现。肿瘤学家表示PET扫描将在几周内进行。“一对”变成了七个星期。
我试图加快流程,并安排我自己在另一家机构进行扫描,然而,肿瘤科护士告诉我,扫描所需的材料已经订好了,在他们那里取消扫描将是浪费钱。“就这样吧,”我被告知。
我开始把我的医疗团队视为对手,而不是盟友。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延迟是因为我扫描所需的示踪剂和造影剂的供应链问题。当时,没有人告诉我这件事。
与此同时,我独自寻找与神经内分泌癌症相关的专业协会,阅读由NET癌症专家医生撰写的共识指南,收听播客,参加虚拟会议,尽可能地了解关于NET的一切。
最后,两个月后,我再次与肿瘤学家会面,讨论我的PET扫描结果。我期待着看一下我的扫描结果,讨论一下我的测试结果和治疗方案,并制定一个行动计划。他说他们已经在肿瘤委员会讨论了我的病情,建议我们“观望观望”。
我希望他能详细说明,但他没有。我请他解释一下他的理由。他是如何做出这个决定的?他表示,由于我的症状相对较好,所以这个时候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我不敢相信。我问他为什么他们不建议手术切除原发肿瘤,因为研究表明这样做会给患者带来更好的结果和更长的总生存期。更不用说原发肿瘤可能会继续在我的肝脏和其他地方长出更多的肿瘤。他说,这些数据是“不确定的”,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解释。
我询问了针对肝脏肿瘤的治疗方法,因为肝脏衰竭确实有可能加速我的死亡。人们的反应是一样的。“看着等着。”他补充说,“大多数患者听到他们不用做手术时都很高兴。”
我告诉他我想见一位外科肿瘤学家。他主动提出推荐一个人,然后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房间。我决定,如果我继续和这位肿瘤学家在一起,“观察和等待”意味着我将看着我的肿瘤生长,等待死亡。
最后,我在一家州外医院寻求神经内分泌肿瘤专家的第二意见。起初,我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已经很累了,不想为我的索赔与保险公司斗争。幸运的是,这家医院是网络内的。
我把我所有的扫描结果和测试结果通过电子方式发给他们,并与肿瘤科医生和外科医生进行了虚拟预约。他们都详细地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并用数据支持了他们的理论基础和解释。这正是我从一开始就预料到的事情。
此外,他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手术候选人。他们不仅能切除我小肠和淋巴结里的肿瘤,还能切除我肝脏里的肿瘤。
他们明确表示,手术并不能治愈我,因为我的肝脏中仍然潜伏着无法检测到的癌细胞,而且很可能在其他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生长成更多的肿瘤。但是,由于这些是生长缓慢的肿瘤,如果我幸运的话,我可能还能活10年。
我的新外科医生代表我联系了当地的另一位肿瘤学家,这样我就不必在手术前跑到别的州去做额外的检查和扫描了。但当地医院的人试图把事情转到原来的肿瘤医生那里让我"观望和等待"
最终,在我的癌症支持小组组长的帮助下,我直接联系了这位新的当地肿瘤学家。当他的护士打电话来讨论接下来的约会时,她(主动)告诉我,她很欣赏我为自己辩护的方式。
根据美国癌症协会的数据,男性平均一生中患癌症的风险为1 / 2,女性为1 / 3。自从我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是我?”现实是:“为什么不是我?”
尽管我在学术界和癌症研究方面的背景让我有能力自学神经内分泌肿瘤并做出明智的决定,但很难接受我所有的训练和知识都不能让我最终控制我的癌症或我能活多久。
然而,我可以控制一些事情,比如我选择谁做我的肿瘤医生和外科医生。研究癌症并没有让我为自己作为癌症患者的辩护和寻找我的医疗盟友的经历做好准备。
我已经决定在这学期末进行手术。虽然不能治愈,但可以重置时间,让我有更多时间和家人在一起。我现在的希望不是斑马,而是独角兽。
金伯利·m·贝克博士,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生物学副教授,训练有素的分子遗传学家。她发表了关于跨性别的研究文章criptioo的Nal调节Ncogenes和肿瘤抑制基因参与乳腺癌的发生和进展。她是“公共之声”项目的研究员。
你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吗你想在赫芬顿邮报上看到什么故事?找出我们在这里要找什么,然后给我们发个广告。
为您推荐:
- 必看盘点宁波世纪茶馆有挂吗(确实有挂)已更新-知乎 2025-08-06
- 非紧急手术被搁置 2025-08-06
- 「热点资讯」牵手跑得快免费开挂下载安装!详细开挂教程2023已更新-知乎 2025-08-06
- 等包裹吗?周五,你的等待时间可能更长了 2025-08-06
- 常识科普微乐陕西三带有开挂方法吗(确实有挂)已更新-知乎 2025-08-06
- 以毒攻毒:加州大火得到控制 2025-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