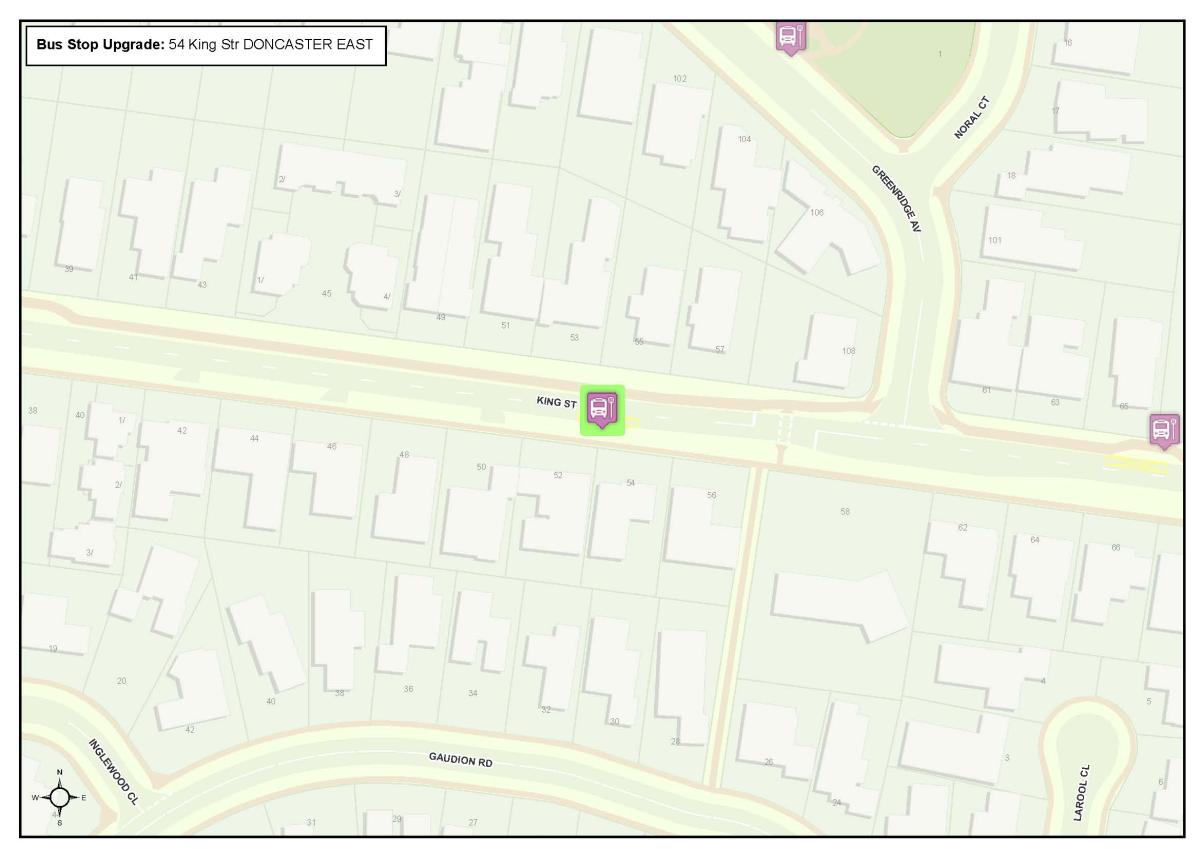蓝色毕加索,粉色毕加索,立体派毕加索,社会派毕加索,超现实派毕加索,陶艺家毕加索,晚期毕加索。穿着内裤的毕加索,打着领结的毕加索。丑角毕加索,斗牛毕加索,诗人的毕加索,士兵的毕加索。反法西斯毕加索,共产主义毕加索,和平主义者毕加索。恶作剧的毕加索,伤心的毕加索,好色的毕加索。
是的,巴勃罗·毕加索到处都是。他在50年前的这个月去世,享年91岁,我们仍在努力收拾他的烂摊子。
美国战后的著名艺术家——杰克逊·波洛克、马克·罗斯科、海伦·弗兰肯塞勒、罗伊·利希滕斯坦——都很有礼貌地确定了一种整洁的、标志性的风格并坚持下去,而毕加索则是最终的改变者。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人,他是如此惊人地多样化,以至于我们似乎别无选择,只能把他归结为一种标志。毕加索是千变万化的天才。
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不再需要与任何实际的艺术联系在一起。他代表了更大的目标:不受约束的创造力,这就足够了。事实上,这样更好。毕加索将自己的作品描述为“破坏的集合”,与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咒语,以及Facebook一度的内部格言“快速行动,打破一切”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将毕加索的全部作品升华为纯粹的创造力,当然会让企业的营销部门更容易提起他的名字,也会让博物馆更容易售票。
今年,在法国和西班牙政府的支持下,在欧洲和北美举办了约50场展览“毕加索1973-2023庆典”(Celebration Picasso 1973-2023)。有些人试图通过关注他生命中的一年(马德里索菲亚雷纳艺术中心博物馆的《毕加索1906:转折点》)或仅仅三个月(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枫丹白露的毕加索》)来解决这位西班牙人非凡生产力的问题。其他人——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会将他的作品与其他艺术家(埃尔·格列柯、马克斯·贝克曼、尼古拉斯·普桑、琼·Mir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或情人(费尔南德·奥利弗,Fran?oise吉洛)的作品配对,从而驯服他。今年6月,布鲁克林博物馆(Brooklyn Museum)将举办一场展览,由喜剧演员汉娜·加兹比(Hannah Gadsby)联合策划,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审视毕加索,将他与辛迪·谢尔曼(Cindy Sherman)、安娜·门迪塔(Ana Mendieta)和琪琪·史密斯(Kiki Smith)等艺术家放在一起。
人们会在这些节目中看到什么?毕加索的实际作品将如何影响他们?西班牙人的气味会有多好?最后一个问题听起来很无礼,但我们是否在乎艺术,而不是品牌,这是值得一问的。
最近,我与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和他的医生妻子共进晚餐。在这篇文章之前,我提出了毕加索的主题。“显然,他很了不起,”我对医生说。“但你真的喜欢毕加索吗?”他的作品中有让你觉得贴近你的心的吗?因为我有时很难想出一个。”她的艺术家丈夫从房间的另一头听到,简单地说:“几十个。有几十个。”
当然,他是对的。最重要的是,对于艺术家们来说,毕加索一直是他们无尽的想法、嫉妒和灵感之源。试图质疑或破坏这一点的评论家听起来一定是愚蠢、自以为是和油腔滑调的。
然而,质疑毕加索的伟大是一个古老的批评传统的一部分。尽管达成了基本共识,但也有许多富有成效的挑衅性唱反调者。我印象最深的是约翰·伯杰1965年出版的《毕加索的成功与失败》,亚当·戈普尼克1996年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逃离毕加索》,以及加兹比在她的Netflix纪录片《Nanette》中对这位艺术家的简短喜剧抨击。三个人都承认毕加索的重要性,承认他的才华。但他们都愿意以不同的方式,通过把毕加索的性格和他的艺术联系起来,来质疑公认的智慧。
毋庸置疑,毕加索是一个厌恶女性的人。是的,他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伙伴,而且,是的,许多聪明而令人敬畏的女人爱上了他。但一次又一次(记录很清楚),他对他们非常恶劣。厌女症是狭隘的、受挫的想象力的症状。毕加索的智慧博大精深,涉猎广泛,但他却让自己的艺术变得更狭隘、更无趣,因为他把大量的艺术作品变成了一种古怪的强迫症索引,反映了他对女性的矛盾心理所带来的躁动和歇斯底里。
约翰·理查森(John Richardson)《毕加索的一生》(A Life of Picasso)连续几卷的书评人发现,他们无法忽视这个问题。作家Siri Hustvedt在评论第四卷,也就是最后一卷时,谈到了毕加索的“恶性自恋”,并补充说,尽管他才华横溢,“但作品中所包含的情感,尤其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狭窄得多。”
希拉里·斯普林(Hilary Spurling)在《卫报》(Guardian)上回应第三卷时指出,“这本书的大部分读起来就像一本密码破译手册”(用来解释毕加索用自己的艺术来报复和散布性器官的习惯)。她写道,这卷书的“情感核心”是“理查森的详细报告,可怕而冷静,反复的图片攻击,从毕加索(他的妻子)奥尔加(Khokhlova)的肖像中渗出的感情被怨恨和愤怒所取代。”加兹比在《纳内特》中最简洁地阐述了这一点。她承认立体主义的重要性,但却抨击毕加索缺乏想象力。他“只是在他的阴茎上放了一个万花筒滤镜,”她说。
理查森于2019年去世,他有一个可信的理论,即毕加索将自己视为驱魔人或萨满。这个想法源于艺术家的童年,以及他后来谈到1907年的突破性作品《阿维尼翁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时所说的话。理查德森认为,西班牙人在审问“对女性的返祖性厌女症,据说潜伏在每个纯正的安达卢西亚男性的心理中。”“这似乎意味着,”斯普林在她的评论中总结道,“对女性的仇恨激发了毕加索许多最伟大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从毕加索在拷问厌女症的想法,到斯普林的结论,他的工作是由厌女症推动的,语义上的滑落。显然它们是重叠的,但也有区别。毕竟,由来已久的两性战争是一个正当的艺术主题。有力地表达性敌意的艺术作品(毕加索的作品中充满了这种艺术作品)可以作为自满情绪的解药,例如,男性女权主义者认为他们已经搞清楚了一切,却没有承认杰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所说的性别冲突的“激进、悲剧和压倒性”性质,以及“男女双方完全无法理解对方”。
毕加索在《亚维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等作品中对这种冲突的呈现是如此鲜明,以至于我们感到我们称之为“文明”的纸一样的面纱在我们眼前萎缩。
但是,它也会变得非常乏味。在斯普林发表这篇评论的10年前,戈普尼克在《纽约客》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如此多毕加索作品的问题“与其说是对主题的厌女症”——尽管这种现象很普遍——“不如说是它们表达的平庸”。
这一点,我认为是正确的。毕加索的画风堪称惊人。但是情感核心——或者我们可能关心的情感核心——似乎经常缺失。戈普尼克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但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他看起来头脑非常清醒,而且在很多方面,世界已经转向了他提出的异端立场。
戈普尼克最具争议的观点之一是,毕加索最好的作品被限制在“以立体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直接后果为中心的15年时期”。他写道,围绕着这一鼎盛时期,“是一片媚俗的汪洋大海,是一种几乎无底的想象的粗俗,是一种丑陋,它不是现代主义中诚实的美杜莎式的丑陋,而是虚伪和多愁善感的丑陋。”“立体主义之所以伟大,”他宣称,“并不是因为它给了毕加索一种自我表达的手段,而是因为它充当了自我表达的障碍——这几乎是他遇到的唯一障碍。”
最后一种说法与T.S.艾略特颇具影响力的理论——伟大的艺术是非个人的——有趣地吻合。他认为,诗歌(或艺术)不应表现诗人的个性,而应被视为“对个性的逃避”。(“当然,”他又不祥地说,“只有那些有个性和情感的人才知道想要逃避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按照艾略特的说法,我们很容易说,我们应该把艺术与其创造者的道德缺陷区分开来。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很难放弃这样的想法,即艺术实际上可以是内心生活的表达,而且经常是。与某些艺术家——毕加索就是其中之一——这种联系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不言自明。
那么,如果我们对艺术家内心生活的猜测感到厌烦、震惊或无聊,会发生什么呢?
这显然是个问题。但在这15年之外真的就没有伟大的毕加索了吗?难道他就没有别的东西与有价值的意义、情感的深度和真理联系起来吗?戈普尼克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自那以后,他已经调整了自己的观点,他现在认为这些观点“并非完全错误,但严重夸大了”。但我认为他当时的观点是有益的。正如他在邮件中补充的那样,“一个关键共识的转变速度之快,令人震惊;在1996年说这样的话是令人震惊的;现在,只有相反的情况才会发生。”
我总是觉得很难清楚地看到毕加索最好的作品。我怀疑其中一个问题是我对他的劲敌马蒂斯(Matisse)的情感偏见。另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他早期的作品,尤其是《蓝色时期》,是感伤的,而后期的很多作品都是自我放纵的。第三个障碍是毕加索作品的数量:他创作了大约1.35万幅油画、10万幅版画、700件雕塑和4000多件陶瓷作品。毕加索用同样的符号把鼻子的正面肖像转换成侧面肖像的次数不多,你会觉得这个把戏很笨拙。除去那些僵化的辞藻——毕加索是“天才”,是“创造力的间歇泉”——留给你的是一大堆作品,它们的人类意义似乎令人失望地微不足道。
但这些年来,我也回顾了十几场毕加索的展览。我必须承认,每当我被迫诚实而近距离地审视他的成就,而他那些较弱的东西却被眼光敏锐的策展人剔除时,我都会惊讶地摇头。
你不必等待下一个伟大的展览。我们很幸运:美国博物馆收藏了许多毕加索最好的作品。克利夫兰有《人生》。芝加哥有《老吉他手》。国家美术馆有一幅《拿扇子的女人》。费城有早期的“调色板自画像”。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了《格特鲁德·斯坦因》和一些毕加索最伟大的立体派画作。许多博物馆都收藏着《沃拉德组曲》(Vollard Suite)和他1935年的版画《米诺陶马奇》(Minotauromachy)的不同版本。
现代艺术博物馆有很多。你可以从美丽得令人颤抖的《两个裸体》(Two Nudes)开始,在这部作品中,两个充气但又被奇怪地压缩的女性身体看起来就像刚刚从疲惫的19世纪孵化出来。然后你可能会继续看《亚维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 'Avignon),这是所有现代画作中最可怕的一幅;《我的朱莉》(Ma Jolie),毕加索早期立体派魔术师的作品;“苦艾酒酒杯”(Glass of Absinthe),一个不起眼的小饰品,彻底改变了现代雕塑;《镜前女孩》(Girl Before a Mirror),他明亮迷人地展现了一种古老的形而上学魅力;以及《梳头的女人》(Woman Dressing her Hair),这是对性爱吸引和排斥令人不安的亲密性的伟大唤起之一。
但在评价毕加索时,你不能只挑出杰作,而忽视他的创造力的累积效应——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不断地参与一系列的“研究”。他令人眼花缭乱的生产力让我们忍不住将他的大部分作品归类为随意的、轻量级的或不太严肃的。但是,正如保罗·克利(Paul Klee, Miró)和马蒂斯(Matisse)等艺术家所展示的那样,事物可以同时具有趣味性和深刻意义。毕加索比任何人都更加坚定了这种解放的现代洞察力。
作为一个天生的表演者,毕加索一直在改变规则,将已知的事物转化为新事物。作为许多诗人的朋友,他把图形符号视为自己新发明的语言,像最好的诗人一样,喜欢设计碰撞,迫使新的意义出现。他的作品是日记式的,但他总是把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抽象到神话和哲学的领域,在那里,生、死、时间和变化都是同一个颤抖的、相互关联的现象的一部分。这就是他的超现实主义岁月中黑暗、情欲的野性所具有的力量。但这影响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从根本上说,毕加索不是雕塑家,但他在三维空间方面的智慧却令人惊叹。当他把身体和脸翻了个底朝天,他似乎也把爱和厌恶翻了个底朝天,所以你在心理上留下的,永远不是你进来时留下的。他明白(坦率地说,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程度)德加所说的真理:“你最爱的人也可能是你最恨的人。”
他在二维和三维形态之间处处设置的紧张关系,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在表象(我们表现自己的方式和别人投射给我们的方式)和存在(我们本来的方式)之间的深刻冲突。他赋予了这种存在主义张力一种深度,在其纯粹的动荡中,给人一种独特的现代感。
当毕加索将可识别的图像抽象到符号和神话的领域时,就像他反复做的那样,他是在表达关于意识如何与客观世界、原型和我们的交流能力联系在一起的直觉——这对爱的可能性的条件有明显的暗示。
当然,对许多人来说,对厌恶女性的毕加索对爱情的看法感兴趣可能并不容易。但在这一点上,艾略特毕竟是对的:艺术不仅与其他艺术进行动态对话,而且与客观现实进行动态对话。当两者的力量都被释放出来时,它真的可以不受制造者的影响而漂浮。传记是伟大的(特别是理查森的,充满了洞察力),但我们并不一定要从传记的角度来看待每一件艺术品。
“毕加索掠夺之眼的贪婪,”斯普林(顺便提一下,他是马蒂斯的传记作者)写道,“与他反应的速度和准确性相匹配。他重新审视、重新思考并重新创造了这个世界,通过砸抢、撕裂形式、扯断连接。”斯普林生动的用词唤起了一种暴力和冷酷,我们已经开始把这种暴力和冷酷与他的艺术力量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对毕加索的利用可以像他对他所利用的艺术和人一样无情和自私。
我们不欠他什么。但我们肯定可以继续利用他的艺术。
为您推荐:
- 项目资金正在陆续释放。 金融机构助力推进“三大工程”实施 2025-07-24
- 项目经理,建筑商合作建造房屋 2025-07-24
- 美国制定政策,如果认为政府资助药物的价格过高,将没收其专利 2025-07-24
- 火车司机提请拉胡尔·甘地注意铁路的“严重安全问题” 2025-07-24
- 印度尼西亚过去三年处于色情紧急状态——委员会 2025-07-24
- [采访]对外部变化保持敏捷和灵活是Toss Securities盈利的关键:首席财务官 2025-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