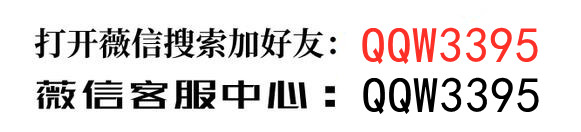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评论过去两周法国在质量方面感觉不同的人。也许西班牙报纸El País说得最好,它评论说这个国家“似乎已经离开了自己”,意思是抱怨已经被毫不掩饰的喜悦所取代。
警察忍不住要跳舞,法国电视台的评论员无法掩饰自己的情绪,psamriphsamrique上的实时交通信息标志都在为lsamon Marchand欢呼,Snoop Dogg似乎一下子无处不在,留在城里的巴黎人放下了他们的冷漠,开始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欢呼;提前逃离的巴黎人发现自己希望自己没有留下来。我听到了《马赛曲》和复古的流行合唱同样自发地爆发出来。十几个国家在维莱特公园设立了热情好客的“房子”,接待了来自远不止本国的欢呼雀跃的球迷,而且主要是免费的。
(另一方面,美国和英国把他们的球队宿舍设置在远离热闹热闹的拉维莱特的地方——“法国俱乐部”和其他十几个欢快的国家馆聚集在附近——入场费分别为325欧元和175欧元。值得吗?由于太穷而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但我怀疑两者都没有达到拉维莱特的派对氛围。)
如果以为法国的混乱和令人沮丧的政治分歧会突然消失,那就太天真了。当然,这不会阻止一大批评论家和一些反对派政客成为悲观主义的永久传播者。但是,奥运会是否会留下一些东西——一些东西,哪怕只是一点点,推动法国讲述自己的故事?
毕竟,心理学家乔纳森·阿德勒认为,故事往往会成为我们的身份。阿德勒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自己视为自己故事的主角。他说:“你先讲故事,然后用自己的方式融入其中。
但讲故事也有消极的一面,比如,它会让我们忘记自己曾经珍视的积极品质。法国经常沉溺于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倾向于几乎难以理解的怀疑主义。2011年的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民意调查显示,法国受访者对未来的看法比伊拉克或阿富汗人更为悲观,这两个国家正在经历战争和暴力——这种深刻而挥之不去的悲观情绪在2014年得到了重申,十年后又得到了重申。
一种解释是,这不是法国独有的现象。已故的瑞典公共卫生研究人员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几十年来证明,西方公众对全球发展的悲观态度远远超过了已经取得的可衡量的进步的现实——中左翼的法国智库让- jaur
基金会(foundation jean - jaur
)最近对这一观察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但法国人以忧郁著称,所以也许从法国知识文化的哲学基础出发,抓住笛卡尔的“怀疑一切”作为解释,会更有意义。(就我个人而言,在经历了法国学术评分制度的两方之后,我确信,那些或多或少拒绝给出超过16/20分的分数的老师,在潜意识里会觉得事情永远不够好。)
第三个建议是,法国人实际上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悲观,他们只是无法进行民意调查,因为他们条件反射性地倾向于选择最具灾难性的选项。但即便如此,如果这是真的,也会揭示出叙事对现实的影响。
我经常感到困惑的是,美国和法国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而在其他方面却截然相反。他们都不安全,但不安全的表现不同。美国向所有人大声尖叫,在任何时候,它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最好的。法国忧心忡忡,担心自己达不到目标,并因此受到评判。
奥运会的形象是有趣的多层的,从会徽(同时是一个女人,一个火焰,一枚金牌和巴黎盾徽上的船的暗示),毛绒弗里吉亚帽子,也是阴蒂,以及闭幕式上法兰西体育场地板上棱角分明的五大洲,从空中拍摄,也形成了一个比武的骑士。同样,也许奥运会本身对法国来说是多层面的,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推动法国的故事。
在一个相当厌恶风险的国家(尽管在艺术方面不一定如此),巴黎抓住了一个巨大的机会。无论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馆举办奥运会,还是在开幕式上——尽管在美国和欧洲出现了主要由极右翼推动的丑闻——86%的法国公众都认为开幕式是成功的。
接下来的一切都促成了一种普遍的惊奇感,这种感觉像河流一样从那个开口流淌出来,我在街上、在咖啡馆的露台上、在粉丝区、在与陌生人的随意交谈中都经历过。当我们遇到某种超越我们的强大事物时,我们会感到惊奇或敬畏。一次日食,一次善举,一位奥林匹克选手将人体推向极限。
敬畏是真实存在的——它可以通过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在大脑中观察到,并带来心理上的好处。也许当我们一起体验敬畏时,它也会带来社会效益。也许它改变了我们讲述自己和彼此的故事。
当法国决定这样做的时候,它会用华丽、热情、老练、天赋和幽默来做事情。这就是外国人在大多数时间里看到的法国,而在过去的两周里,法国人一直在通过世界的眼睛看待自己。如果我必须给2024年巴黎奥运会打个分?20/20。在这里,我们希望法国队拿着他们赢得的金牌,带着它奔跑。
亚历山大·赫斯特是《卫报》欧洲专栏作家
为您推荐:
- 最新教程“微乐湖南麻将万能开挂器”确实是有挂 2025-07-22
- Android新推出的“强安全性”生物识别技术规格绝非如此 2025-07-22
- 必看盘点杭州都莱有挂吗(确实有挂)-知乎 2025-07-22
- 本田,讴歌联合赛车活动,使他们更接近勒芒 2025-07-22
- 常识科普德扑之星辅助器软件!(详细开挂教程)-知乎 2025-07-22
- 京华mp3,重新定义音乐体验! 2025-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