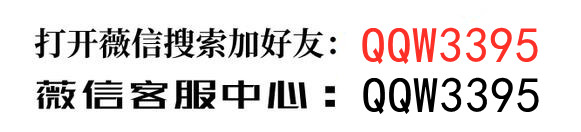我永远不会知道我去了多少次墨西哥。
每次回来,我都完全不知道我曾经去过的地方。
除非使用组织者派给我的运输工具,否则我不能移动。
我从来没有独自旅行过。
那一次,陪同我的是那位伟大的墨西哥作家
安东尼奥Ortu?o(他的小说)
人力资源
,胡安娜·维亚尔主演,
最近被改编成电影)。
我们最初是在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见面的,Ortu?o注:2016年左右的书展。
每当我试图回忆起一件遥远的事情时,我就把那段奥德赛称为“征服健忘症”。
这一切是发生在瓜达拉哈拉还是墨西哥城?
Ortu?o记得当时的环境和人物,但显然我们像墨西哥流浪乐队一样喝酒,哈利斯科风格,直到我们忘记了时间和地点。
假设那是在我公务活动结束的时候。
在墨西哥城的一个酒吧里。
突然,从一张坐着六个人的桌子上,他们正在唱歌和喝酒,嘲笑开始向我涌来。
我不太明白这是玩笑还是邀请,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在墨西哥的走廊里,我想我听到了一些布宜诺斯艾利斯口音的痕迹。
阿兹特克文明是无穷无尽的。
Ortu?o告诉我,一些西班牙投资者聘请他担任一部关于征服的迷你剧的顾问,但支持阿兹特克的传统制片人过多,阻止了他继续参与。
从那张桌子上传来的尖叫声中(这是佛罗里达战争的典型过程或后果),纳瓦特尔语与西班牙语并无区别,后者是雷加尔语或拉丁美洲语的变体;
这是一个多方面的融合,被mezcal霸权化和同质化。
最后他们说出了我的姓,我走近他们。
有人拥抱我,有人亲吻我。
原来他们是哥伦比亚组合Los Pachanga及其衍生品,他们的旋律我是在派对上、在电台里、在超市里演奏时知道的。
在此之后的5年多时间里,这种音乐一直高居榜首。
每次他们宣布名字的时候,我都默默地想:“我不喜欢帕查加。”
但
不是因为我评判他们的音乐,而是因为我个人对舞蹈过敏,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反射行为
.
其中一个萨克斯管乐手和主唱原来是我七年级的同学。
还有墨西哥、波多黎各和萨尔瓦多成员。
他们在西班牙语世界巡回演出,既成功又有趣。
但阿根廷人说服了其他国家,在那次聚会上
我应该为他们写一首波莱罗舞
.
他悲伤的歌,像Hernán cortsamas悲伤的夜晚。
他们从来没有用慢节奏表演过忧郁的爱情故事。
我是被选作活人祭品的人。
我问他们付了多少钱,他们回答了最后喝了一杯龙舌兰酒
.
但我坚持,有人提到我不知道有多少微不足道的版税,这可能会让我变得富有。
我当然接受了。
虽然我真正唯一担心的是歌词真的会被唱出来。
在我已经老去的生活中,我开始怀疑存在一个平行的宇宙,在那里,我曾经写过的、兑现过的、永远消失在虚无的架子上的剧本和歌词,最终被生产出来并被解释。
他们要我的电话联系方式,三天之内我会给他们一个理由。
在一次致命的宿醉之后——显然,我吞下的虫子帮助我活了下来——我寄出了波莱罗的初稿。
它的标题是:
给我时间
.
我让自己受到胡安·加布里埃尔(Juan Gabriel)的歌词的影响——受地域渗透的影响——但他突然出现了一些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抽象。
因为"让我们给自己一点时间"这句话更符合胡安·加布里埃尔的变化和字面意思,但是
给我点时间
揭示了某种,不夸张的,隐喻性的野心。
男孩们喜欢它。
然而,和往常一样,他们表达了反对意见:从我的笔迹推断,这对“花了一些时间”的夫妇无法和解。
事实上,他们都要求归还失去的时间。
而歌手认为这对情侣应该在波莱罗舞曲的结尾见面。
我回答说,那就不会是Hernán科特萨梅斯的悲伤之夜了,我引用了他自己的话。
但他坚持说,既然我们都是阿根廷人,我们完全可以把科特萨梅斯放在一边。
不一定,我不紧不急地想:很少有对话场景比承包商和作者之间的交流更类似于cort
和蒙特祖玛之间的对话了。承包商在看到文本后,惊呼“我喜欢它”,并立即应用了一系列截然不同的修改它的指令。他困惑地看着自己灵感的破灭。
我不知道是什么恶魔把我迷住了,我站在我那绝望的短上衣上,寄了一封新的信给那对仍然分居的夫妇。
歌手Conintes邀请我去他家烧烤,吃玉米饼,地点在墨西哥城的某个边缘地带,我从来不知道,也不会知道那是墨西哥城的外围还是中心。
当然,他应该接我去当司机。
这对夫妇住在一座带花园的豪宅里。
她是阿兹特克人。
这两个男孩和女孩有着不同的文化和口音。
他们是一个游牧家庭,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Tenochtitlán。
帕查加的短上衣应该以欢乐结束。
在某种程度上,我似乎明白她是在暗示她自己的爱情。
或者她的自爱。
我告诉他我会考虑的,这又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在回来的路上,
Candilejas
,通过
卡洛斯
突然,不知从何而来,我想起了我们公立学校七年级的两个阿根廷人组成的双人组合Sensación,就像毕业旅行筹款活动的一部分。
在我们在坦迪尔的那一周结束时,两位母亲中的一位带着四位父亲中的一位逃走了。
也许是那个插曲,我现在才想起,就好像一个巫师把它从我的记忆中抹去了几十年(征服amn
西卡),以这样一种方式伤害了康尼斯,以至于他想用一件神奇的上衣来改变结局?
那个不眠之夜,我一直想着我的短上衣,夹在莫特祖玛和科特萨姆之间,不想背叛,也不想徒劳地战斗。
但我失败了,我在黎明的第一缕曙光中睡着了,如果你把它称为太阳试图出现时笼罩墨西哥天空的烟雾云(也许被征服者永远击败了)。
我带着电脑里的一首未发表的歌词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在飞机上,我时而被一种尊严的光环包围着,因为我没有放弃对波莱罗的肤浅的想法,时而又被我一贯的悲怆所包围。
我心满意足地着陆了。
几个月后,“帕查加”的另一位阿根廷成员瓦拉达雷斯(Valladares)给我寄来了康内蒂斯创作的波莱罗舞曲,并明确要求保持沉默,以纪念这位自杀者。
瓦拉达雷斯和康尼斯从小学毕业就开始约会了
他们并没有为各自父母的闹剧感到特别不安;
也不是康尼斯在墨西哥建立的家庭。
但两年前,就像在胡安·加布里埃尔(Juan Gabriel)的波莱罗(bolero)里一样,巴拉达雷斯曾向孔蒂斯提出一段时间的要求,以为他们会以新的热情再次见面。
康涅狄斯再也没能从这段感情的间歇期中恢复过来。
他责备巴利达雷斯和他自己,直到他痛苦而不可挽回的结局。
瓦拉达雷斯心照不挂地指责我,是我的短上衣引发了这一结果
.
帕查加部落解体了。
给它一点时间,我想。
我没这么说。
也许我应该让自己以一个快乐的结局来结束歌词……但我发现自己身处一片陌生的土地,那是夜晚,罗伯托·卡洛斯的收音机正在播放。
在WhatsApp的音频中,我不时地听到Conintes y Valladares根据我的歌词创作的美妙歌曲,我把它保存在一个由我自己组成的小组中(不是哥伦比亚或衍生品)。
在那个平行宇宙里倾听她的上帝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
为您推荐:
- 一位患有厌食症的女性为了欺骗体重秤而戴着砝码,她跑得太多以至于腿都断了 2025-07-20
- 简单学会“贝贝捕鱼有挂吗(详细真的有挂)-知乎 2025-07-20
- 玩家必看教程“圈子游山东麻将有挂吗”分享用挂教程 2025-07-20
- 建立成长中心,稳步发展 2025-07-20
- 今日教程“蜀山四川麻将外卦神器”确实是有挂 2025-07-19
- 倒卖泰勒·斯威夫特的票赚大钱?国税局会知道的 2025-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