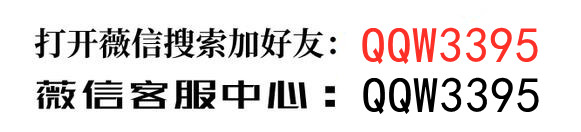这名23岁的学生抗议者被关押在尼加拉瓜一所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在这三年里,他从未见过阳光。狱警经常殴打和折磨他,最后还扯掉了他的一只脚趾甲。
凯文·索利斯(Kevin Solis)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在一夜之间把他释放了,也不知道他要去哪里,这时一位美国外交官拍了拍他的背,微笑着。
“结束了,”那人说。“不要再受苦了——你自由了。”
索利斯跪在停机坪上哭泣。
后来,在飞机上,222名持不同政见者欢欣鼓舞——一些人相互拥抱;其他人欢呼鼓掌。许多人流下了难以置信的泪水,在一个温暖的二月夜晚,他们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在长达数小时的时间里,空乘人员会恳求乘客坐下来系好安全带,但他们对这些命令置若罔闻。它们是免费的。
当飞机从首都马那瓜的奥古斯托·c·桑迪诺国际机场(Augusto C. Sandino International Airport)起飞时,坐在索利斯旁边的男子拍了拍他的肩膀,敦促他往窗外看。
“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看到这片土地,”总统候选人、前大使阿图罗·克鲁兹(Arturo Cruz)对索利斯说。“他们剥夺了我们作为尼加拉瓜人的权利。”
两个人哭了。
这次飞往哥伦比亚特区的“自由飞行”载有相当一部分尼加拉瓜被监禁的政治精英,在更大程度上,还载有反对西半球最专制政府之一的反对派运动成员。其中一人是美国公民。
乘客中有六名有抱负的总统候选人、知识分子、活动人士、记者和著名的前游击队员,也有学生领袖、护士,甚至还有一家大型报纸的司机。这些人在以登机为条件获释后,被剥夺了国籍。今天,他们正在努力在美国建立新的生活。
大约在飞机起飞前一周,尼加拉瓜政府曾向美国驻尼加拉瓜大使凯文·沙利文(Kevin Sullivan)表示,如果美国同意接收这些囚犯,尼加拉瓜愿意释放他们,并强调在移交完成之前,释放这些囚犯必须保密。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对记者说,随后与国务院进行了快速谈判,转移囚犯的秘密行动开始了。由于讨论敏感的外交问题,这名官员要求匿名。
2月9日降落在杜勒斯国际机场后,这两名尼加拉瓜人获得了人道主义假释,每人获得了300美元。这些前囚犯的年龄从20出头到70多岁不等,后来在26个州定居,其中最大的群体在佛罗里达州、马里兰州和加利福尼亚州。
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十几名前囚犯讲述了他们所遭受的身心折磨的细节,其中一些人是第一次接受英语媒体的采访。
现在,当他们试图从监禁中恢复过来时,他们正在努力在美国找到自己的立足点——从适应外国文化到找工作,再到满足住房和医疗等基本需求。更艰难的是,他们被迫与家乡分离,并为他们的家人感到恐惧,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国家在远方分崩离析。
一些人希望,他们的解放将是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和他的妻子罗萨里奥?穆里略(Rosario Murillo)政权屈服于国际压力,停止迅速升级的侵犯人权行为的一个迹象。
但在大规模释放后的几周内,奥尔特加政府只是加强了其威权控制。它又剥夺了94人的国籍,包括著名作家吉奥康达·贝利和塞尔吉奥·Ramírez,并拘留了至少一名记者,因为他们报道了复活节庆祝活动,这违反了一项禁止公开表达宗教信仰的新指令。
当56岁的主教罗兰多álvarez当天拒绝登机时,政府将他从软禁转到监狱,并以叛国罪判处他26年徒刑。他也被剥夺了尼加拉瓜公民身份。当教皇方济各谴责奥尔特加迫害天主教领袖时,总统暂停了与梵蒂冈的关系。
今年3月,联合国一个专家调查小组发现,奥尔特加;他的副总统穆里略;其他高级政府官员犯下了广泛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法外处决、任意拘留和酷刑- -这些都是出于政治原因对平民犯下的危害人类罪。
调查负责人扬-迈克尔·西蒙(Jan-Michael Simon)将尼加拉瓜强制流放的做法与“苏联和纳粹德国犯下的行为”相提并论。
他说,在拉丁美洲漫长的独裁统治历史中,最近没有像尼加拉瓜这样大规模驱逐的先例。
西蒙对《华盛顿邮报》说:“奥尔特加摆脱了他的整个反对派,我不知道在拉丁美洲有任何类似的大规模案例。”
索利斯在大学时是一名法律系学生,也是组织反政府抗议活动的积极分子,现在他在旧金山写了一本关于他在豪尔赫纳瓦罗监狱(Jorge Navarro Penitentiary)的书,在那里他一年没有见过母亲。晚上,他在一家害虫防治公司工作。
索利斯在2020年被判处5年半监禁,罪名是在抗议期间抢劫一名政府支持者,索利斯否认了这一指控。即使是现在,他每晚也只能睡两个小时,一直认为是时候进行例行审讯了。
“谁是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谁在资助反对派运动?狱警和监狱长会这样要求。他说,当索利斯拒绝回答时,他们会扇他耳光,剥光他的衣服,用警棍打他。殴打经常发生在一个星期两到三次。
援助尼加拉瓜人的组织酷刑受害者中心(CVT)的美国临床项目主任lsamuonce Byimana说,近三分之二的前囚犯患有身体或精神健康问题。拜马纳补充说,虽然许多持不同政见者都在与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作斗争,但该组织很难为他们找到医疗服务。
尼加拉瓜人描述了可怕的监狱条件,其中一些人被单独监禁长达三年,许多人被剥夺了阳光,睡眠或足够的食物。那些被关在同一个牢房里的人不允许互相说话,有时甚至不能窃窃私语或吹口哨。不允许阅读材料,甚至连圣经都不允许,这导致一些人记住了饮料和其他物品上的成分标签。
其他人则用手势相互交流。
他们都告诉《华盛顿邮报》,他们被长期与家人隔离,这种待遇违反了有关囚犯权利的国际公约。
Lesther Alemán还记得自己清晨在监狱中痛苦地醒来,因为“还有23个小时要在绝对的寂静和黑暗中度过。”为了活下去,这位学生活动家——他曾在2018年与奥尔特加对峙,这是出了名的——会回想自己生活过的每一年里最美好的时光,他最喜欢的电影场景,他曾经喜欢过的书的段落。他甚至虚构了一个假想的朋友,取名为拿破仑。
现年25岁的Alemán于2021年被捕,被控“阴谋破坏国家完整”。在以恶劣和不卫生条件而臭名昭著的El Chipote监狱里,他的饮食是14颗豆子,三勺米饭和一个煮鸡蛋作为早餐和晚餐。他说,他瘦了很多,以至于当他躺在水泥板上时,都能听到膝骨相互撞击的声音。他和妹妹住在迈阿密,目前正在努力找工作。他说,就连填写工作许可的基本文件都很困难,尤其是询问国籍的那部分。
“我把这部分留空,”他说。
Alemán和Solis是36名曾经被监禁的大学生中的两名,他们现在生活在美国。
42岁的塔玛拉Dávila是一名女权主义活动人士和反对派领袖,她在埃尔奇波特监狱被单独监禁了14个月后,在拥挤的空间里遇到了麻烦。许多知名的反对派政治领袖都被关押在那里。她还在努力找工作,她说她负担不起体检的费用。
今年3月,Dávila从夏洛特来到华盛顿,在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发表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演讲。她讲述了2021年6月12日晚上,数十名警察冲进她在马那瓜的家,把她打到脸上流血——尽管她辩称自己没有拒捕。
她被单独监禁了14个月,她的女儿在被捕时只有5岁。她对《华盛顿邮报》说,这次分离太痛苦了,她进行了为期五天的绝食抗议,这样她的女儿“就会有一天知道她的妈妈为了见她做了一切。”
Dávila在美洲国家组织的发言中指出,美洲人权法院- -西半球最重要的权利监测机构- -要求立即释放她,但没有效果。
达维拉对美洲国家组织代表说,她很感激自己重获自由,但无法完全掌握或享受这种自由,这与许多前囚犯分享的事实相一致。这些异见人士生活在一种无国籍的不稳定状态中,远离亲人,他们说,他们感觉被困在了一个自己没有选择的国家,一个无论如何都欢迎他们的国家。
胡安·洛伦佐·霍尔曼·查莫罗是主要反对派报纸《新闻报》的首席执行官,也是颇具影响力的查莫罗家族的一员,他被控洗钱,被关押了545天,但他否认了这一指控。当他在杜勒斯机场与女儿团聚时,他欣喜若狂。
但喜悦很快就变成了苦乐参半。
“我很快意识到我是出狱了,但我不是一个自由的人,”霍尔曼说,他现在和他的嫂子住在弗吉尼亚州的维也纳,在等待工作许可的同时,他正在努力找一份工作。“我不自由,因为我不能说我想说的话,也不能做我想做的事,因为我担心我仍在尼加拉瓜的家人、妻子和朋友。”
他的银行账户被关闭,国籍也被吊销。他从所有公共登记处消失了。
“就好像我从未在尼加拉瓜存在过,”他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完全的民事死亡。”
虽然少数囚犯是富有的、有影响力的家庭成员或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意见领袖,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那么幸运。
据前囚犯和尼加拉瓜活动人士估计,至少有一半持不同政见者在美国没有任何关系、朋友或亲戚,大多数人不会说英语,最终依靠非营利组织、教堂和陌生人的帮助。对一些人来说,无根感和绝望感可能会压倒一切。
45岁的卡拉·帕特里夏·维加和57岁的桑德拉·阿塞韦多都是护士,她们在2022年11月入狱的第一个晚上相遇。他们很快就因为对孩子的爱而联系在一起,成为彼此的保护者。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维加回忆起2018年尼加拉瓜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时,她如何跳上摩托车,给十几岁的儿子送去食物和燃烧弹。她说,她想“确保他有更好的机会在政府的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在暴力镇压之后,他逃到了哥斯达黎加,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或听说过他。
最近,她参加了“秘密”会议,并帮助组织了抵制2021年总统大选的在线运动。她被控“阴谋和传播假新闻”,被判处8年监禁。
在她们前往华盛顿之前,这两名妇女都没有离开过尼加拉瓜,也没有乘坐过飞机。现在在马里兰州银泉市,他们没有计划,也没有钱,他们说找工作甚至上公共汽车似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在这里感到绝望,”阿塞韦多流着泪说。“我不想待在这里。我宁愿躲在尼加拉瓜的某个地方,在那里至少我能被我的人包围。但我在这里该怎么做?我们从哪里开始呢?她说。
CVT的Byimana说,至少有一半的前囚犯没有稳定的住房,170人身无分文,至少50人濒临无家可归。
他说:“他们付不起住房、药费,什么都付不起。”“他们中的许多人依靠当地的食品银行,好心人。他们基本上活了下来。”
拜马纳说,他的组织已经要求美国政府让这些前囚犯与他们仍在尼加拉瓜的家人团聚,以保护他们。
他说:“他们在尼加拉瓜的家人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们了,这是造成他们压力和焦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比他们遭受的酷刑更严重。”
美国国务院在给《华盛顿邮报》的一份声明中说,国务院“充分认识到”尼加拉瓜人面临的挑战,并呼吁采取立法行动,“将这些人的身份转换为难民身份,这样他们就有资格获得比目前人道主义假释更多的福利。”
人道主义假释身份不适用于家庭成员。
奥尔特加(77岁)曾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的领导人,在1979年推翻了美国支持的索摩扎独裁政权,这是他第四次连续担任总统。他还在20世纪80年代领导过这个国家。
他对2018年爆发的广泛暴力抗议活动进行了残酷镇压,并从那时起系统地针对批评者和反对派领导人。根据美洲人权委员会(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的数据,至少有350人在抗议活动中丧生,数千人被投入监狱。
被监禁的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是他的前战友,神秘的桑地诺“游击队员”多拉María tsamulez,被称为“二号指挥官”,他在22岁时领导了1978年尼加拉瓜国家宫殿的传奇风暴。
桑地诺政权掌权后,tsamillez成为卫生部长,但几年后开始批评奥尔特加的独裁倾向。2021年6月,这位退休教授和历史学家因“破坏国家主权”被判入狱8年。
67岁的tsamllez说:“奥尔特加走上了成为独裁者的道路,效仿索摩扎。”在这条道路上,他必须面对我们所有人,我们多年前就决定与所有独裁政权作斗争,这一直是我自己的道路。”
tsamllez和她的兄弟和侄子住在乔治亚州的萨凡纳。在El Chipote被单独监禁605天后,她因缺乏平衡和皮肤色素沉着等健康问题接受了治疗。
“你很快就被释放了,但离开监狱需要时间,”tsamllez在谈到适应过程时说。“但当务之急是生存、康复,并继续与尼加拉瓜正在发生的事情作斗争。”
她说,在游击队的岁月帮助她度过了流亡的挑战,因为她具备了其他人可能缺乏的“纪律性、清醒的头脑和耐心”。
“与年轻的异见人士不同,我以前看过这部电影,我知道它的结局,”她说。“奥尔特加走了。”
今天,奥尔特加和71岁的穆里略几乎控制了政府的方方面面,包括国民议会、最高法院、武装部队、司法部门、警察和检察官办公室。尼加拉瓜人可能会因为挥舞抗议者的旗帜、在Facebook上发帖或参加复活节游行而被捕。政府关闭了独立的报纸、电视和广播新闻节目。
目前生活在流亡中的221名尼加拉瓜人中的大多数是在2021年11月总统选举前夕被拘留的,那次选举为奥尔特加轻松获胜扫清了障碍。
自由航班上的许多乘客都希望奥尔特加执政的日子屈指可数,他们中的政治领导人决心继续他们的斗争。他们接受媒体采访,撰写报纸专栏,并在全球民主论坛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演讲中谴责政府的专制行为。
虽然一些在美国遭受迫害或非法监禁的政治难民可能将流亡视为重新开始的机会,但这些中美洲持不同政见者却梦想有一天能够返回尼加拉瓜。
“我想回去,因为我的一切,我的幸福,都与尼加拉瓜的命运密不可分,”著名学者、曾经的总统候选人f
利克斯·马拉迪亚加(f
lix Maradiaga)说。
马拉迪亚加现在和妻子女儿住在迈阿密,他计算着自己作为自由人的时间:3月底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他已经有1200多个小时了。在被关押在马那瓜的611天里,他养成了以分钟和小时计算天数的习惯。在他获释近四个月后,他承认自己对自己的自由感到矛盾。
他说:“作为自由人的一小时,就是其他人在监狱里度过的一小时,我忍不住为此感到内疚。”
查莫罗政治家族成员、前总统候选人胡安Sebastián查莫罗将自己20个月的监禁和获释比作“死后复生”。与马拉迪亚加一样,他被指控“破坏”尼加拉瓜的“主权和自决”。
查莫罗是尼加拉瓜反对派民主与正义公民联盟的前主席,也是尼加拉瓜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目前与妻子维多利亚住在休斯顿。他们都打算继续谴责奥尔特加政权的反民主行为,并返回尼加拉瓜。
“无论这一事件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么痛苦,有多么孤立,”他说,“尼加拉瓜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梦想是作为自由的男人和女人回去。”
为您推荐:
- 玩家必看教程“微乐河南麻将万能开挂器”其实确实有挂 2025-07-17
- 强力推荐“微乐广西麻将小程序必赢神器免费安装”(原来确实是有挂) 2025-07-17
- 今日实测“全来湖南麻将开挂方法”分享用挂教程 2025-07-17
- 一分钟教你“wepoker作弊版本”其实有挂 2025-07-17
- 一分钟教你“掌上麻将圈到底有没有挂”分享用挂教程 2025-07-16
- 今日分享“微友陕西麻将其实是有挂”分享用挂教程 2025-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