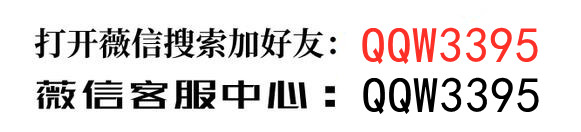民主党的信仰是什么?这很难说。2024年,乔·拜登(Joe Biden)和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发起了一场温和、和解、强调恢复制度规范的竞选活动。与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不满狂欢相比,这未能引起公众的太多关注。在失败后的几个月里,民主党人对如何最好地进行下去感到困惑、矛盾和内部争议。
结果是相互矛盾和无效的。民主党人时而宣称特朗普是法西斯主义者和准独裁者,时而祝贺自己和平地把权力交给了他;他们抨击他的腐败以及他对未经选举的南非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服从,但他们也愿意与马斯克的项目合作,以削弱联邦官僚机构,并为他自己的利益重塑它,这项倡议被愚蠢地称为“Doge”。
他们承诺抵制特朗普主义者接管国家,然后承诺在他们坚持的共同优先事项上与特朗普合作。“我怀疑我们可以在某些问题上找到共同点,”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说。惠特默经常被认为是未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你必须正视问题,”来自佛蒙特州的左翼旗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说。“不能简单地说,‘哦,这是特朗普的主意,我们反对。’”
你会注意到,这是美国政治的一种愿景,在这种愿景中,民主党没有权力自行设定辩论的条件,也没有权力推进自己的优先事项:只有极右翼才能提出政策建议,而民主党人只能对这些建议竖起大拇指或竖起大拇指。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竖起了大拇指。民主党人跨党派投票支持川普的内阁人选,不少于12名民主党参议员投票支持川普的反移民拉肯·莱利法案。
2017年的狂热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时特朗普首次上台激起了左翼的复兴,并鼓励当选的民主党人用激进的媒体、法律和程序策略阻挠新总统的破坏性议程。现在,民主党似乎更像是默许,而不是抵抗。他们没有对特朗普咄咄逼人、施虐成性的使命提出任何有意义的反对。相反,他们只是翻来覆去,就像一只顺从的狗露出肚子一样,时而把这种姿势视为对宪法秩序的原则性承诺,时而将其视为一种不幸的必然性,他们不能为此受到指责。
越来越多的政治评论员将2025年的民主党比作二战时期法国的纳粹通敌维希政府。“这是一个因投降和失败而诞生的政权,”时事通讯《不得人心阵线》的约翰?甘茨写道。“这是一个天生疲惫、虚无主义和玩世不恭的政权:对共和国的旧真理失去了信心。”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之际,民主党人似乎最希望的是再次回到2012年。他们希望奥巴马联盟回归;他们想要以前的规范和制度程序的精细;他们希望两党合作成为一种美德,他们希望被视为理性、务实和冷静。他们希望特朗普,以及他的崛起给我们的政治世界带来的变化,永远不会发生。

在过去两周重新掌权的极右翼,据说正着手逆转20世纪,摧毁其在种族平等、妇女权利、同性恋尊严和自由以及民主公平方面取得的进步。但是,如果说共和党人正在寻求逆转20世纪,那么民主党人似乎只想忽略21世纪。他们的策略和冲动,他们对美国政治如何运作的看法,在现在已经不起作用了。他们似乎不去适应未来,而是把头埋在沙子里,等待着过去的回归。
阅读更多
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党人没有适应政治沟通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选民可以被他们的信息环境所激励和说服:民主党人一次又一次地转向右翼,利用报纸、有线电视新闻和新闻稿等传统媒体来展示他们的新立场,并与自己的立场保持距离。选民们看不到这一点;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忙得不可开交,共和党人在社交媒体上巧妙地制定议程,民主党人只能勉强跟上,把对手逼得更右。结果是,该党多年来一直没有主张自己的实际世界观:民主党人没有表现出一套社会价值观,或一套治理理论,或任何类似于对原则的承诺。他们没有为目标群体挺身而出,也没有表达出真正的民主愿景;他们从来没有选择勇敢的战斗,他们从来没有采取立场,当共和党人反对时,他们不会退缩。难怪美国公众一想到民主党人,就倾向于认为他们脱离现实、投机取巧、懦弱。那是因为他们是。
结果,与其说民主党是一个较弱的政党,不如说他们根本就不算是一个政党:是极端的共和党人,而且只有他们,在向公众传达美国的愿景,而那些假装“反对派”的呜咽、卑躬屈膝的政客们,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愿景来反驳,只是悄声地、几乎听不见的微弱回应:“还没有。”
民主党人现在需要的是找到他们的脊梁,并阐明一套他们不会退缩的价值观。关键不是试图假装他们认为选民已经同意的立场:关键是要坚持原则和正直的立场,并让这一指导方针吸引选民。
选举是受欢迎程度的较量,而受欢迎的方式不是通过政策,而是通过个人的坚强,通过愿意进行斗争。如果民主党人打他们长期以来认为会输掉的仗——变性人权利和堕胎;保健和儿童保育;教育;社会保障;很好,工会的工作——他们可能会发现,正是斗争本身证明了它的说服力。他们已经尝试过妥协;他们已经尝试过投降。是时候尝试反抗了。
莫伊拉·多尼根是《卫报》美国专栏作家
为您推荐:
- 布丽·拉尔森主演的《艾丽卡》是一部奇怪而无聊的戏剧 2025-05-07
- 1分钟学会“微信小程序微乐河北麻将外卦神器下载安装!详细开挂教程已更新-知乎_足球_体育_喜临门 2025-05-07
- 加沙停火的下一阶段充满不确定性 2025-05-07
- 今天2月15日的星象让天秤座在他们不需要的东西上超支 2025-05-07
- 通用工具“功夫川麻怎么开挂免费”(原来确实是有挂) 2025-05-07
- 最新教你“众乐联盟开挂辅助软件!详细开挂教程已更新-知乎 2025-05-07